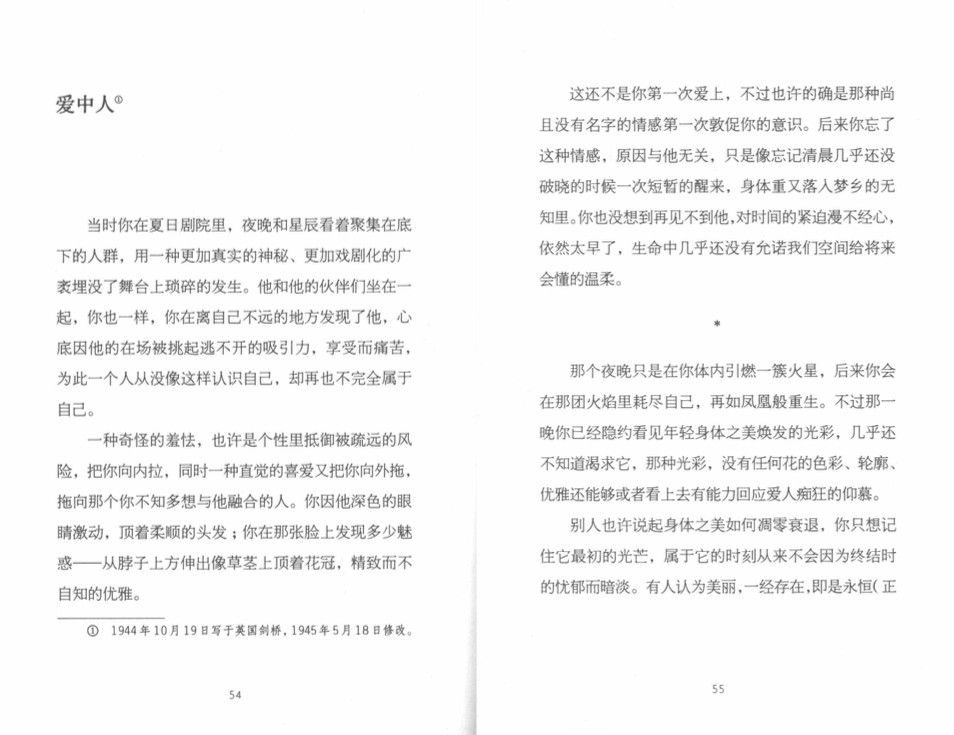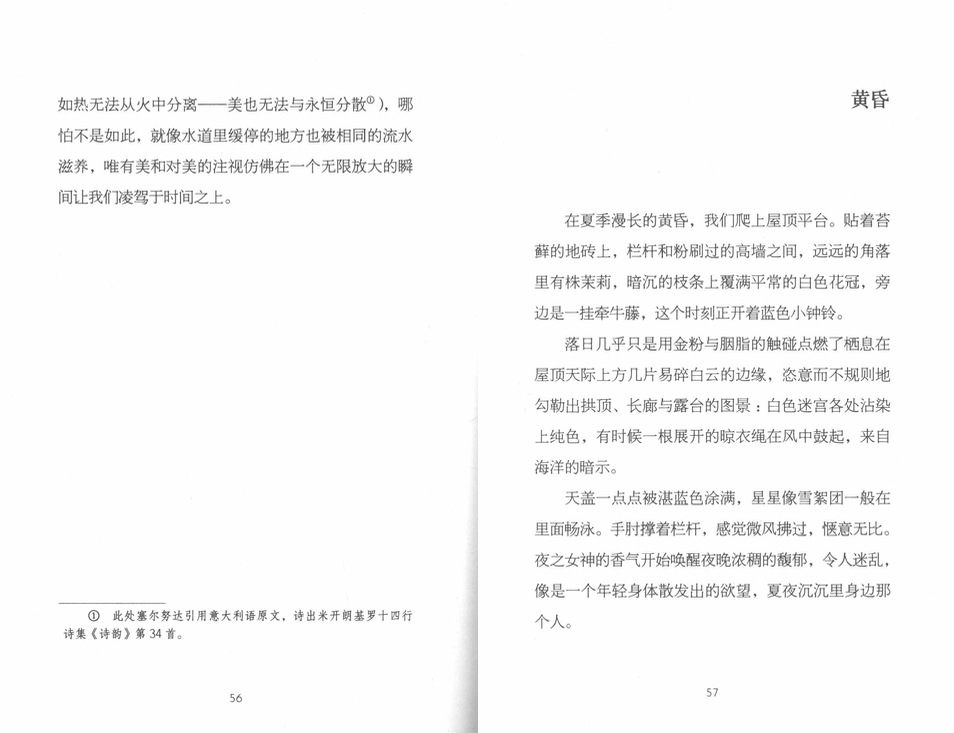#20170815
效率不低地忙了大半天学校工作、小半天策划工作。和 Y 到他朋友的酒吧喝了小半杯威士忌。到家第一件事儿,扎进箱子就把《活着活着就老了》拆出来。
冯唐自述,诗第一,小说第二,杂文第三——我挺喜欢他的杂文。《活着活着就老了》断断续续翻过一些章节,最近想着为写博文、写杂文摸摸语感和定位,于是在又一轮网罗中把《活着活着就老了》终于买下来。相比技艺奇巧或仙风道骨的写作者,我喜欢热腾腾的人。
一个日本朋友送了我一张巨大的纸,纸的大标题是二十一世纪,下面密密麻麻地列了从2001 年到 2100 年的每一天。他想用这张纸劝我的是,珍惜光阴,努力奋进。
我在这张纸的面前站了一阵,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在这密密麻麻的日期里面,必然有一天是我在人世的最后一天。我想到的是:
第一,绝不在无聊的人和事儿上浪费时间,哪怕一天。
第二,继续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推进医疗的进步,缓解人类肉身的苦。
第三,呼吸不止,写作不止,老老实实地放开写,能写多少算多少,看看还能写出多少人性的黑暗与光明,缓解自己和他人内心的苦。
第四,少见些人,多读些书。见人太耗神,做幕前工作我蠢笨如猪,在书里和写作里,我游得像一条鱼。
#20170815 视听笔记
「迟早更新」#30「红红火火恍恍惚惚」(100mins)★★★
- 风投圈、创业圈是由上层决定的行业。有了上层,支撑、刺激、诱导下层。
- 共享单车的资源可移动性低,容易无法对接需求,虚假数据影响到使用体验,且要按它所声称的,以「公共出行解决方案」的要求来要它 /滴滴与 Uber 模式调动已有的闲置资源,资源来到你面前,使用体验更真实、更好;
- 钱是个符号,它代表你能调动多少社会资源。你不需要拥有它,只需要负责调动它。
- 在这个事情没有崩掉之前,每年亏两亿和每年挣两亿是一样的。
- 商业价值是建立在社会价值上面的。只要是想通过认认真真服务别人去挣钱的,就是好创业者。什么才算是好的创业公司呢?开得越久越好。
- 「好」是一根线,只要过了这条线,就都是好的。很难在线上再做什么比较。
- 「互联网化」要比「互联网+」更加精准。互联网上的业务是真实世界中所有业务的互联网化映射。网上本身没有空间的概念。游戏业也不是什么互联网的原创,不过是原有游戏以及赌博行业的延伸,而其中的「多媒体」则是一种技术,它和互联网是两个行业。
- 文娱/娱乐和内容是两个产业。在内容产业,大家消费的是被留存下来的、值得留存下来的内容。文娱/娱乐行业消费的是关系链,内容只是辅助建立这个关系链、这笔交易。直播不是内容行业,它是娱乐行业、夜总会业务的互联网映射。问题是,「直播」是否有可能向内容、向社交行业发展?个人认为,它向社交行业发展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内容依托于形式(e.g.《驴得水》的话剧与电影版,小说的电影版改编、漫画的动漫改编不要求观众调动大量想象力,更受欢迎;),它对互动性的要求极大,有些内容是没有这个属性、需求的,没有必要创造需求。
- 研究「第一名」、谁是第一名、为什么考第一,这是研究中的一种错觉。考第一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任何人都有可能考第一,所以它不独特,不值得研究。反常的事情才值得研究:以少胜多,突出重围......
#20170816
和 Longlong 约在颐堤港吃铁板烧,席间又聊到内容创作。穿了阔腿裤和平底鞋,天气也阴沉,状态就放松,放松到不知不觉又口无遮拦地吐起槽来——我似乎有一种总能在公关面前口无遮拦的恼人天赋——好在 Longlong 体谅得很,一边夹肉过来,一边顺着话茬调侃,「我也真是很难想象你如果进了一家公司工作,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呢,我当然有自己想进或者至少说想进进看的公司。我也没接着辩驳,心里倒是感谢 Longlong 的这道提醒:组织、机构、企业究竟是什么呢?——我还是感激当它们可以作为「准线」,作为冷酷的「牵制」。人的浪漫不在永恒,而在短视。庞大而非人的机制则能把个体从盲目中牵制。大的逐利,总比小的逐利、逐的小利要好些,独立状态下的个人太容易选择后者。
更无可避免地,我们聊到博主生态。我迫不及待地把在前几日博客提到过的竹子、飞猪带货一事讲给她听,Longlong 格外平静,「你要知道,作为普通读者和作为公关,我们认可一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言下之意,竹子、飞猪的所谓转化率随高,但其所基于的搭建模式实在成本太高、机制过于复杂了,最重要的,其可控性太低。商业总显得淘气,总显得错开人的预判起码半拍,多数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将之想得太过精巧?在以货品而非虚拟产品作为筹码和指标的这部分商业世界里,我们都要开始尝试说服自己。
Longlong 见我的第一句其实是,「之前听朋友提起你,说是在某次航班上与你邻座,正好儿和你聊了天儿,她说你特别有趣。」——很开心。最关心的,莫过人们是否能够在与我有进一步深交后,获得起码不会比此前更糟的体验——是体验,不是印象;对后者的把握都不过是猜忌,何况诉求本身就是自我中心的、镇压式的单边计划。像昨天写,「相比技艺奇巧或仙风道骨的写作者,我喜欢热腾腾的人。」,我当然也希望自己能够被作为「热腾腾的人」而去喜欢。我多少懂所谓「技艺奇巧或仙风道骨的写作者」是多么孤独、敏感而不可靠。忍不住再引雷晓宇写朴树——「这不是他的机会,这是他的命运。这是一个拥有天赋者的精神危机和通向自身的旅途。」——很喜欢这篇文章。一半原因来自雷晓宇笔锋所留下的割痕剃削有度,一会儿让创作粘连在情绪上,一会儿又把成长和衰老放进不同时空;另一半,我纯粹敬仰「机会」和「命运」这独一幅措辞——「他让我突然间读懂许多歌词」顶多算可怜可爱,「他让我开始相信命运与归途」的道理我最近才懂。对天赋者、创作者,实在找不到比「机会」、「命运」更精确的代指去配合这场针对其生命的完全解剖。分明同样的事件,因为一种狠不下心来的「自欺」,就以最骄傲的方式,用顺从和默许去取代一路伴他而来的胜负欲。一下把生涯和生命分开,读不得,见不得。
今天同样延续了最近的状态,除去工作没做什么别的。下午两点在新元素配着鹰嘴豆酱三角豆饼点 Merlot 喝,真是累到一定境界了。
#20170817
一无设计美感二无历史背景,Balenciaga 把 Kering 六个字母印在纯色 hoodie 上就敢售价 650 美金成为秋冬新款,真不知道是现代商业社会默认圈钱可以无底限,还是开云这偌大招牌认为自己只值这点钱?
在朋友圈看到,觉得与在「无状态」播客第 1 期里和李茶、Sam 讨论到的「杜尚」问题在本质上是同一个。用一句话来拢括,就不妨借用「得意忘形」第 18 期的标题:「宇宙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记录者,就是宇宙本身」——所谓「一无设计美感二无历史背景」,因为其「历史背景」是隐形的。设计身前身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即包括设计师、设计史身前身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其记录者就是设计本身。我们之所以说 Vetements 就创作本身而言是反民主的、是精英主义的,多半在于公众面前它那幅懒懒散散、睡眼惺忪的样子,太多话要讲了,所以呢,懒得和你讲。所谓古怪的 misfit 感,诞生于你明知道有什么东西在那儿却未经提点、难以悟及的夹缝空间——我这样讲,有点像是在说奢侈巨头就是 21 世纪的小便池:实用,常见,下流,但在迁移之下,又有泉的美感。我也有必要纠正一下,不能说 Balenciaga 把 Kering 六个字母印在纯色 hoodie 上,Balenciaga 是把 Kering 的正规 logo、trademark 印在 hoodie 上——这二间的区别是巨大的。到了 20、21 世界的当口,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呢?所有创造都是迁移,一件帽衫或许在表面上走了符号迁移的捷径,骨子里迁移的最少是当代艺术的方法,而从当代艺术开始,又是一道又一道的曼妙递归。
第一次在秀场上看到这件 Kering 帽衫,我是被惊住的,以一种赞许的方式。一是 trademark 的力量和魅力横冲直撞地扑过来拷问你,二是_这个_ trademark 的力量和魅力横冲直撞地扑过来拷问我。幸运到几乎让人相信所谓宿命的,在因被 Hedi Slimane 吸引而关注行业后的不久,他回到 Kering(当时还叫 PPR)的 Saint Laurent。和 Saint Laurent 中国部门日渐熟悉是我为数不多的真正企图,并不侥幸地,也有幸实现。Richard 默默推荐我去为 Kering 大中华区做有关新生代青年文化、消费文化的报告,至于后来给了我不少工作机会与宝贵经验的 Gucci 团队等等,就坐在当天房间的后排——那是三年前,我十六岁。我穿着快时尚品牌三四百块的高跟鞋,在南京西路假装潇洒,一脚深一脚浅地疾步快走。在静安嘉里对面的路口,第一次试图点燃一只爆珠。
足足经过三个月和大概三十道工序,一小箱印满 Kering 标识的纸本文具作为致谢漂洋过海地来到我手上。Kering 六个字母的样子是怎样落在本面上,笔杆上,烛台上,上海总部会议室的墙上,我始终记得清清楚楚。
晚上和朋友吃饭,又一次在空荡荡的金融街留下很多所谓思考、劝解和质问。回家路上特意绕去 711 买了瓶酒精含量足有 15% 的梅酒,计划着回家坐下来踏踏实实地完成日志。等真的坐好,脑子里只升起一句话大声回荡:「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读者也好,朋友也好,恋人也好,每当有人说「你变了」,我总紧张得不行。论紧张,一是因为我从未向任何人分发过类似结论,因此对这样的叮咛格外敏感,总觉得其背后有者久久潜伏、终于爆发的隐秘动机,或者,就在我眼皮底下,栖息着什么我本人视而不见的万丈深渊;第二点,从未分发,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懂——要谈什么变化,那总是要有静止起点、起始状态的吧?提出如此苛责的人,要不就是自诩认知了你的本真状态,要不就是脆弱地希望你们之间的关系回到那个足够亲密以至于 TA 足够认为曾一度接近你本真状态的时刻。是可爱的自负、可爱的脆弱,但人总要为自己而前进,这总不会错吧。
「你变了」,「你变了」,「你变了」,我还是走到现在了——谈不上明朗,可「问心无愧」、「还算开心」这样的词都未免太含糊而中性了。在由「性格压力」所主导的设定里,「不变」远比「变了」要可怕许多。我看过许多站在原地的人,不论是向前探身而难以行进的,还是安然端坐甚至寻找着靠背的,任何一种静态都令人恐惧——在全平台更新了前两天翻译的《深度学习时装周》,是最近难得舒服的事。
想引一段阮一峰老师。
问:你的博客早期都是谈文学的,怎么会转变为一个技术博客?
大学里,我喜欢读小说和传记,曾经以为社会科学是自己一辈子的专业方向。后来发现,在中国搞社会科学没前途,除非愿意给政策背书。那时,我还喜欢写社会和政治评论,每次都有一大堆互相争吵、人身攻击的留言,无法得到任何结论。我还接到过有关部门的电话,要求删除文章。
最终,我觉得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之类的学科,都没多大用处,就渐渐不想走这条路了。它们也不是真的没用,就是在中国不行,改变不了现实,只会让自己走入绝境。在我看来,走技术这条路至少有一个好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在国内,)如果你想不撒谎、不干坏事、并且被公正地对待,那么可能你只能去编程了。”
问:很多人批评你的技术文章,错误非常多,你怎么看?
我一直是外行,从来不敢说自己是专家。对我来说,博客首先是一种知识管理工具,其次才是传播工具。我的技术文章,主要用来整理我还不懂的知识。我只写那些我还没有完全掌握的东西,那些我精通的东西,往往没有动力写。炫耀从来不是我的动机,好奇才是。
当然,我肯定只写那些我觉得对的东西,尽量对读者负责。但是没法保证,我觉得对的东西就是对的。网站流量越来越大,对我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好几次我都在文章前加上说明,这是初学者的笔记。我还会以这种方式写下去。我希望自己永远都能保持,那种不怕丢面子,敢于当众说蠢话的勇气。
同样一场饭局,又听到有关你的信息,哭和笑都那么合适。Xinyao 替我气,说怎么还不快把他拉进黑名单。我说,我是诚诚恳恳地认为,我实在没什么好怕。尴尬当然,但我一步不是靠什么不明不白的关系上位,二是这些所谓的走漏也不可能让任何东西不再站得住脚,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去畏缩。那些「我可真是傻逼!」怎么会不是空骂?性格压力也好,自我压力也好,创作和目标上,我只肯把自己束得紧紧的,可拉再紧也箍不到的那部分的自己,到底还是要去护着。我不断地听说,不断陷入胆战心惊,不断地确认,不断地又深陷苦闷。周而复始,我也始终只是觉得自己浪漫,浪漫得惹人发笑而已——浪漫又什么错的呢,何况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都还年轻,我也看得不到在未来的哪个时刻,我会不再年轻。当我踩着便宜的高跟鞋一脚深一脚浅地在南京西路大步地走,我就永远地学会年轻。
推进了一些工作,拖欠着一些工作——从上海回来后的每一天,明明都可以如此简洁、精准、优雅地带过——至于那瓶梅酒,又一次再两点钟接通 L 的电话,又一次聊了小一半通宵。就着娇嗲,喝了七成。
#20170817视听笔记
「一天世界」#56 iPhone 十周年——期待与反省(50mins)★★★
- 以 iPhone 面世为标志的移动互联时代才刚刚到来十年,即使考虑到当今时代更迭速度加快的因素,十年对社会学研究来讲也是一个相当单薄的时间周期,我们当前的论述可能都还十分稚嫩。电视在 50 年代已于美国迎来全盛,可直到 80 年代,才有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出现。
- 苹果硬件与软件上的呼应与配合,整体优化使用体验;
- 独立这件事对当下的 iGen(iPhone Generation)来说,不那么有吸引力了。e.g. 为公路旅行而学车/频繁使用 Uber,没有必要学车;
- 怀疑精神、反叛精神在他们身上变得稀薄了,怀旧狂潮盛行。e.g. 大众偶像 Taylor Swift 制作 80 年代风格的音乐,作为这一世代的时代的偶像,却没有提出超越先前时代等类似的宣言;地下、亚文化界流行着的是古董合成器风格;油画已经变成某种手艺、工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了。它有太过丰富的历史去研究,本身已经不再鲜活,其打造过程也不再像是艺术创作,而更像是去设计——音乐也似乎在向这一方向发展。很多音乐,拿掉梗,就什么都没有了。随商业化的指引,音乐成为游戏行业等的配器。
- 当前时代的特点是,我们处在、沉浸于在这个时代之中,但我们从普通民众的角度也同时在反思这个时代。整体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得意忘形」#29 聊咏春和费曼之间顺便破解一下学习的真谛(110mins)★★★
- 如果对一个东西,你想学得更快、理解得更深,或者说他人的讲解你无法理解,那么就应该去找一个看似和它特别不相干的事情,去学,去融会贯通。e.g. 网球/咏春,身体力度的松与紧、放与收;
- 下棋,很久没下,但因为人的成长,棋力反而上升了。放一放,但你对身体、对自己、对学习、对世界的理解加深了,从一些死循环中跳出来了,且你其实带着问题,在生活中进行观察和思考了。
- 什么时候你知道自己的研究进入正轨了呢?——当你吃饭,喝水,睡觉,看一切都有有关这件事的启发和影响,都是你这一课题的案例、表象、解决方法。只有在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的研究才进入了正轨。
- AI 的问题,没有 transfer-learning(知识迁移),它一定需要大量的、专门的数据,每次训练都要从零开始。
- 强的球队不是你在状态好的时候能胜对方一个 5:0,而是在你状态特差的时候还能赢下一个 1:0。不需要有妙手,每一手都 85 分就能达到高手。发挥这种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拼一个长跑。
- 对自我的要求:多用「比喻」。(知识迁移)
- 在学习东西的时候要用一种信心,老师可以只是作为为你提供信息的人,但你可以自由地将信息重构地学习,然后 self-educate(自我教育)。
-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
- 「Keep your identity small.」(少为自己贴标签,少围绕标签去做事)——当你认同某个标签,这个标签就将极大地影响你的思维,将你向某个方向、某个结论去推。创作是来自于表达你内心里的某些东西,而一旦拥有「标签」,你则将开始为了外力去「演」某个人。
- 诺贝尔奖得主在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往往无法继续做出同样高质量的研究。在盛名之下,他们不得不选择宏大的、似乎是诺贝尔量级的重大问题去解决,而事实上,真正的诺贝尔奖级别研究往往都不诞生在这样的课题之上,而其实是种子,是那些未被完全认知、开发的小点。同理,风口创业。费曼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持续为本科生讲课,他说每一次讲课都为他带来重新的认知。他说他无法为本科生讲清楚量子物理学,这代表他还完全不懂物理。他对「什么叫做理解一个东西」有着极高的理解。
- 费曼技巧 + 费曼解题法
- 两种天才:能理解他的天才本身,他的速度、敏感比我好一百倍;无从理解,本身是一个「黑匣子」,无法为它的思维方法建模。
「科技聚焦」#32《聚焦》:从购买音乐到流播服务,订阅制的狂潮才刚刚开始(40mins)★★★
#20170818
雷阵雨的一天。和袁里、肖恩、皮埃约在三里屯,从傍晚到天黑。看到黄景行,还有总是引起皮埃赞叹「真是幸运男/女孩儿」的、手拎「喜茶」的、三五成群的路人。去西五路吃泰餐。可算单穿了前一次还是出现在台北夜聊时的真丝吊带短裙,因为极高的开衩而被蚊虫频繁叮咬——之所以放弃了「去 Dada 蹦一会儿」这个持续了大半周的念想,大概正是在当身上六神花露水味儿盖过「幻想之水」的时刻开始酝酿。我们靠在竹藤椅上有一搭儿没一搭儿地聊八卦,松松垮垮。袁里抽中南海,本来就不重的味道被北京难得的潮湿气息再次稀释,传到斜对面的我这里,暧昧又困倦。喜欢这样无须被填满的大段空白。
照例一起逛了店。想买白色的 Tabi 高跟靴和 Vetements 的深黑灰色牛仔长裤,想买 Supreme 的合作款滑板挂在墙面。想买 Dior 那顶皮质的贝雷帽,等头发养过肩膀的冬天正好戴上。
两点入睡的作息持续了一周,十点就成为精神最活跃的时刻。今天的十点,刚好卡在刚刚吃完饭的当口,干这也不是,去那儿也不妥,就听着后海大鲨鱼磨磨蹭蹭地走回家,在麦当劳发呆。去逛酒,拎了一罐儿黑豆浆出来。
和皮埃说,「我觉得我还要一会儿,才能走出来吧。」——而在此之前,试图清醒总是好的。在彻底清醒后,它会让你显得稍微不那么愚笨。
#20170818 视听笔记
「(Hi)story」#1 裸体不是同性恋者和女人的专属义务(70mins)★
#20170819
最近的身体状态很怪很怪。不来一点甜腻就晕眩和发抖,可摄入一丁点糖分都不会适得想呕。解决办法是大口喝含着碎冰的巧克力饮料,有苦涩和冰片稀释后得热量变得十分可靠。
还是午间才起来,骑车到国贸,趴在桌子上一边用冰巧续命一边听塞尔努达的散文诗集《奥克诺斯》。写了会儿博客,再花上一个半小时走路回家。在清醒的白天,实在无法处理那些逼迫我面对「认知偏差」的工作——对自己的认知有偏差,对行业的认知同样也有。正是这二者相叠而成的那扇空间构成了营生的来源。
读到冯唐写,好得足够挤进文学窄门的文字需要幼功、师承、苦难。